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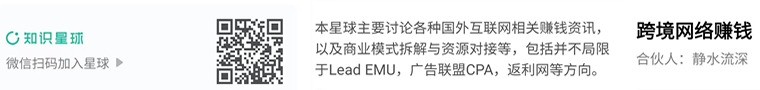
2004年12月17***12:28 来源:中华读书报
作者:王培元
舒芜先生的《一个小女子的生死》,是篇好文章。好就好在它剥下了曾国藩这个大人物的华衮,披露了这个头上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清代“中兴重臣”鲜为人知的另一面,显现出他的岸然道貌和冷酷、自私、伪善。
或有人云,过去士大夫哪个不是妻妾成群?像这个平民出身的陈氏小妾,嫁了曾国藩这样的达官显宦,算她有造化。谁叫她福分浅,进门只几个月,便一病不起,死了的?对于曾国藩这样的“巍巍乎高哉”的大人物,纯属“生活小节”,小事一桩嘛。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!
是的,老爷、大人作威作福,子女玉帛,从来如此,天经地义。大凡读过一点古书,就都知道的。《尚书.洪范》不是早就说过,“唯辟作福,唯辟作威,唯辟玉食”吗?天有十***,人有十等,上贵下贱,男尊女卑,古中国社会就是不把人当人,尤其是不把女人当人。妾媵制度历史古久,从老祖宗那会儿就开始了。“役人贱者,男曰臣,女曰妾。”儒雅的士大夫者流,更是蓄姬纳妾,把女人当作玩弄、役使、污辱、淫乐的对象。
“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。”为什么要孜孜矻矻、皓首穷经、十年寒窗、萤雪苦读地爬上去?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……书中自有黄金屋……书中有女颜如玉”,这首据说是宋真宗赵恒写的《劝读诗》,明明白白地指引了目标。就是要爬到“治人者”“役人者”“享福者”“享乐者”的地位上去。要知道,老爷、大人们欲得而享之的“福”,除了“寿”“富”“康宁”“攸好德”“考终命”的“五福”(《尚书.洪范》)之外,还有人所津津乐道的“艳福”哩。
王谠《唐语林》卷六有云:
韩退之有二妾,一曰绛桃,一曰柳枝,皆能歌舞。初使王庭湊,至寿阳驿,绝句云:“风光欲动别长安,春半边城特地寒,不见园花兼柳巷,马头惟有月团团。”概有所属也。柳枝后逾垣遁去,家人追获。及镇州初归,诗曰:“别来杨柳街头树,摆弄春风只欲飞。还有小园桃李在,留花不放待郎归。”自是专宠绛桃矣。
以儒家“道统”的正宗传人自居、口不离仁义的韩愈,不愧是文采风流的一代文宗。只是不知道弱小的女子柳枝,为什么竟敢从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“道济天下之溺”的大文豪家里逃走?被追获后又怎样?但有一点大约是可以肯定的,被抓回来的柳枝,遭到主张“民不出粟米麻丝、做器皿、通货财以事上,则诛”的韩大人的冷落,失宠了。
“古所谓媵妾者,今世俗西北名曰‘祇候人’,或云‘左右人’,……而浙人呼为‘贴身’,或曰‘横床’,江南又云‘横门’……”庄绰在《鸡肋编》里说的,怕只是一般的妾。而能歌善舞的绛桃和柳枝,她们只是主人“可狎而玩之”的工具、玩物而已。只有好好侍奉主人,忠于主人,“克尽职守”,才能博得主人的欢心。像柳枝那样不安于“贴身”“横门”的姬妾地位,主子当然不会高兴了。于是乎,“专宠绛桃矣”。
由此亦可知,另一位古代大诗人白居易,为什么会写下“燕子楼中霜月夜,秋来只为一人长”的《燕子楼》诗,叹赏尚书张愔的爱妓眄眄的“念旧爱而不嫁”,又写了“黄金不惜买蛾眉,拣得如花三四枝,歌舞教成心力尽,一朝身去不相随”的《感故张仆射诸妓》诗,感慨家妓不能为死去的主子陪葬了。
正是这个写过《上阳白发人》《陵园妾》《琵琶行》,曾为沦落天涯的长安倡女泪湿青衫的白居易,晚年阔起来以后,曾大肆蓄养家妓,其中最广为人知的,就是所谓“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”的樊素和小蛮了。这实在是令人艳羡不已的一桩雅事,诗人自己亦颇佯佯自得。而且,这些以色艺事人的女孩子,每过个三年,白诗人就嫌她们“老”了、“丑”了,于是打发掉,换旧更新,再买一批年轻漂亮的进来,十年间,居然换过三次之多。而且,还要赋诗把此事专门记述下来:“十载春啼变莺舌,三嫌老丑换蛾眉”(白居易《追欢偶作》)云云。
难怪舒芜先生看到这样卑劣不堪、令人作呕的文字时,忍不住愤怒地斥责道:“说得这样得意,这样自夸,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,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!”“这是少见的无耻恶劣”! 见《哀妇人》第369页 骂得真是痛快淋漓!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