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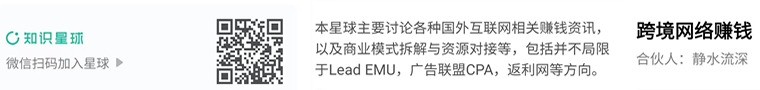
有一种感觉,就像真理一样刺痛着我。没错,真理一样的刺痛。
常常我会被一些东西刺痛,这些东西在当时或者现在就是象真理一样。在这里,我所说的“常常”不是指时间总和的多少,而仅仅是一个频率。事实上它们就是许多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事情里面的间隙瞬间,就像我现在关了电脑关了灯,半躺在床上,借着定格的电视画面的亮光,用一只某KTV的广告笔,在一本盗版的石康的书中最后那一页白纸上写字一样。这些字让我灼痛,而这我又给了自己一个理由,就是在一首不知名的电视插曲中听到的一句:anytime I find myself。
今天的早些时候,当我空下来对着电脑感到无聊、闷躁、犯困,抽烟又晕烟,咖啡喝到有点想吐的时候,我又习惯性的新建文档,用小六号的宋体敲打着一些我现在已经忘的一干二净的文字,希望能够缓解自己当时那种极其不舒服的状态。也很坦然的说,这种虐待文字,亵渎“文学”的做法,在过去,现在,还有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将来,对我都是行之有效的,起码现在的我无法、不能否认和推翻这一点。,甚至我现在所作的事情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那一点。当然,文字本身是不懂的悲哀的,只有想它,写它的人会,也许某些读它的人也会。我只是在反省自己,反省自己在从事一个几乎每天都和文字狼狈为奸又相依为命,必须靠文字裹住赤身填饱空腹的工作之后,自己对文字的那种赤诚的态度的改变。而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回忆,回忆一种被我自己称之为“单纯”的一种东西,就像自己忘了什么时候写下的一样:我趴在一丝不挂的大地上写字,一个女子从身边走过,燃烧成我最后的灵感,单纯的文学梦,随着她的脚步飞扬,消失。
同样记不清是什么年纪的自己,只要想到一句自己觉得好的字句就会马上用笔写下来,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,只要我有能够用来写的东西我就一定会下来(也就像我现在写字一样)。但是现在,这个面目狰狞的现在,我已经极少这样了,更多的时候更是连“想”也懒得去想。我觉得这和我的工作有关系,但是不必然,尽管在此刻之前我一度一定这是必然的,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“想”,而且往往很累,所以我在空下来的时候就是要不去想。当然“不想”不是我说不就能不,在客观上那是不可能,毕竟“想”这种东西,尤其是对我这种人往往是无法自控的,我所说的不想只是一种态度上的不。我会把许多时间花在看球赛,看动漫,看电影,看电视剧,寻找和下载各种资源上。但是很不幸和失败,时间在这种层面去说又是很漫长的,漫长的让我愤怒,它长的足够让一些你无法停止的“思想”操控着你在里面迷失、悲伤、疯狂,又或者感到一切无从说起。这种“思想”我一度有着记录的习惯,因为我真的局的那样很美,我会用我的文字去捕捉它们,更每每随着思想的触角蔓延开去(顺便罗嗦几句,现在我已经在一本中国电信免费派发的《点击》上继续写了,刚才的一页已经正反都写满了),描绘出一些让自己会让自己兴奋的画面,或者是写出一些自己觉得不可一世的经典字句。但是现在,我称自己得了致命的残疾,我已经丧失了那种能力,就从自己对文字的态度发生不知不觉的“恶性”转变的时候我就丧失了那种能力。我痛苦,也痛恨自己那么清晰的知道这一点。捕捉到一些想法,但是才写了几句就无法写下去的沮丧、无奈,让我彻底的沦陷,甚至无法在心中真正的宽恕自己无辜伤痛的心。
I never free,I never me,突然又想到这句这些日子老在脑海打转的歌词,也霎时想起了自己曾经是个热爱音乐的孩子,想到自己能在各种形式的、只要自己喜爱的音乐中被感动被震撼,会随着开到最大音量的音乐进入忘情的境界。“我用音乐与世隔绝,我用音乐与灵魂连接”,我也会把自己在音乐中经历的一切化成文字的歌唱,并形成自己的想法。可是现在,我害怕,我在音乐中战栗!我害怕自己残忍的看着它们在自己的笔下挣扎然后夭折!
我总觉得我现在写的这个东西是仅仅为自己而写的,但其实又不完全是,我知道自己会在某个时间把它敲到电脑里,然后用自己觉得臭屁的不得了的态度“给会看的人,让懂的人懂,让不懂的人不懂”将它们贴到网上。所以在我打算结束这次对我来说久违的,不亚于奇迹的狂草乱书的时候,我要交代一句,也是为自己交代一句,这只是我突然的抓狂,是我的睡前臆想症恶性发作,无需认真对待。 |
|